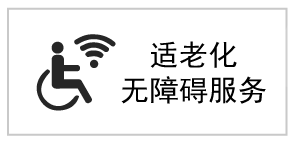|
虹川旧事丨民国乡绅胡奉尘与居士林
|
|
胡奉尘先生,(1887-1950)字天朴,号耐翁、耐道人,虹桥杏庄人,民国乡绅。精通道、释、儒三教,对诗词歌赋和书法深有研究,造诣颇深。他才高八斗,剑胆琴心,胸中有丘壑,笔下生云烟。他以慈悲为怀,救助弃婴孤儿。热爱国学,撒播文明种子。造福桑梓,热心公益事业。一生中做了许多好事善事,被民间广泛传颂。 1923年,胡奉尘与张云雷、吴莉宾、胡奉佛、胡寿彭等乡绅同建虹桥居士林,(俗名净土堂),张云雷和吴莉宾共捐田产31亩为居士林林址,弘扬佛法,提倡净土法门。居士林内设救济院、孤儿院、国学讲习所,聚集着一批喜欢研读佛学、国学经典的文人雅士和地方贤达,延请国学大师高谊、朱鹏主讲国学,并请天台名宿谛闲上人主讲佛学经典。当时虹桥镇上一批有影响力的老字号:王德大、姚同升、姚春和、蔡日升、倪振昌、伍万兴、赵恒泰、陈大丰、杨万丰、颜广丰、悦来等商行的掌柜,易经风水师林浩士先生(七村原虹桥木器社旁边)以及貌桥头的张大生国药号掌柜张仲珊先生、东街的尚华先生等人,都是“居士林”的门生。南洋佛教领袖竺摩法师(俗名陈德安)在孩提时代,天资聪颖,生性洁净,曾随其尊父陈永旺(号红梅居士)多次前往河深桥村附近的居士林听经学佛,幼濡国学。 胡奉尘先生倡建的“居士林”,俗称“净土堂”,位于虹桥镇南面虹河西路的南端,河深桥村的对岸。为一个四合院式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隔成多个房间,有客厅、茶室、雅间、读经堂等。后院建有两排厢房,分别为孤儿院和救济所。侧院建有厨房、储物间及猪栏间、厕所。1923年建成后,虹桥的乡绅贤达、文人雅士,云集此处,吟诗诵经,琴棋书画,品茗对饮,讲经悟道,好不悠雅!居士林还建了孤儿院,又称“育婴堂”,收养贫苦人家的弃婴及孤儿,花钱雇请数位“奶娘”来孤儿院给孩子们喂奶,其爱心被乡人称道。居士林还设有救济所,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食宿。居士林有一个施粥棚,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熬几大锅白米粥,为穷苦人家及流浪汉、过路的云游僧人施粥。胡奉尘先生广结善缘,与镇上的商贾、大户人家均有交集;他的书法一流,骨格清奇,刚劲俊逸,为虹川儒雅绅士所喜爱,吸引着一大批书法爱好者,在居士林品茗吟诗、挥毫泼墨,一时传为佳话。在他的倡导下,虹桥形成了学国学、学佛学、发善心、做善事的良好氛围,居士林成为虹桥文人雅士、骚人墨客雅集的文脉宝地!有钱人家每月捐点银子,作为居士林慈善事业的开支费用,支撑着孤儿院和救济所的正常运行。这种经世致用的行善方式,既便在今天看来,不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对口帮扶,精准扶贫”的具体体现吗? 胡奉尘先生现尚存世的书法题刻有数处,一处在白龙山顶龙水喷景区“清云道观”的老门台石刻楹联,“青山堪䍩道,云水得大观”,落款为“林浩士撰 耐道人胡天朴书”,白龙山石板宫的门台上,有一石刻楹联:“此地绕千秋风月,偶来做半日神仙”,落款胡天朴。现存貌桥头七间巷张大生药店传人张维荣先生家有一块长条形黑底金字木刻牌子,上书“中医张仲珊诊察处”八个行楷大字,另一处刻于湖边双桥寮廊柱上,再有就是东横街口天一药店的“天一”石匾,以及乐清市区西门楹联:“无缘不到此;有福方同修”。砺灰窑村台门联:“其人拟曹许;所乐希孔颜”。长山龙圣寺山门楹联“龙天拥护,圣众同居”。题卢霞九墓联最多。这些存世的题刻,弥足珍贵! (胡奉尘先生手迹 虹桥长山龙圣寺山门楹联) 解放初期的1950年,胡奉尘作为大地主,以花甲之年娶十八岁媛主小老婆的罪名,被人民政府逮捕,是当年震惊虹桥的首批被集中枪毙的“十八个头”之一。据说当时的河北省长胡开明,又名胡昆(虹桥杏庄人)得到消息,要枪下留人,可惜晚了一步,没来得及阻止行刑,胡奉尘先生便被枪决了。他的财产和土地被人民政府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他的小老婆,当年仅二十岁出头,也被政府分配给虹桥二村四十多岁的农会民兵、未婚农民倪阿贵为妻。 1993年夏季,喜欢书法和收藏古玩的虹桥一村叶华桂先生与我一起,曾专门去石帆霞雪村的后山“覆船山”一带寻找胡奉尘先生的坟墓,我们扒开比人还高的草丛,披荆斩棘,沿着石头小路,找到了胡奉尘先生的墓地,站在墓碑前,向先人鞠躬致意,表达我们对先辈雅士的敬意。 解放后,居士林被政府没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作为东联乡人民公社的驻地,后来此地改成虹桥制革厂、虹桥节日灯厂的厂房。老房子现破损严重,建筑原貌破坏殆尽。作为民国文脉的传承之地,居士林曾经闻名遐迩,名人纷至沓来。影响力之大,享誉海内外。我在想,什么时候能让蒙尘的居士林洗涤尘埃,再现昔日的辉煌? |
 浙江政务服务网
浙江政务服务网